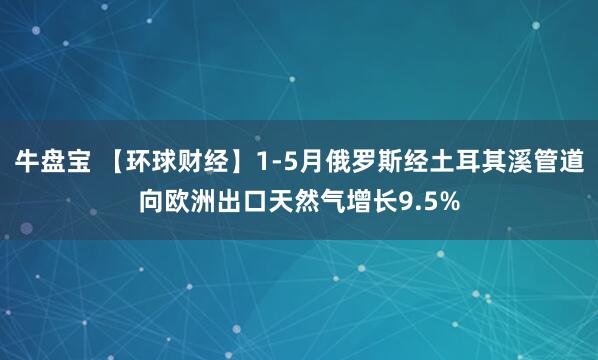文丨喜盼晴亿正策略
编辑丨一池秋水
前言
几年前,英国罗尔斯·罗伊斯公司还在高傲宣称哪怕破产,也绝不把核心技术交给中国。
可三年后,这家百年老牌的航空发动机巨头却悄然改变立场,主动提出在中国建厂,还公开表示“愿意开放部分关键技术”。
曾经拒绝中国200亿元投资、拒签5000台发动机大单的企业,如今终于发现——离开中国,它活不下去。

曾经的“航空之王”:宁破产也不与中国合作
如果说欧洲工业有几颗象征性的“王冠”,那罗尔斯·罗伊斯无疑戴着最耀眼的一顶。
1914年,第一台鹰式发动机点火,改变了航空史的命运。
二战时期,名震天下的梅林发动机更是让英国空军赢得不列颠空战。
彼时的罗罗,代表着世界发动机制造的巅峰。

几十年过去,罗罗仍然傲视群雄。
它的遄达系列发动机,为空客A330、A350、787提供动力,市占率一度高达35%,与美国的通用电气、普惠并列三大巨头。
英国人引以为傲,媒体更是称它为“帝国最后的工业奇迹”。
但傲慢的种子早已种下。中国自2000年代起多次提出合作意向,罗罗总是高高在上地拒绝。理由冠冕堂皇——“技术安全”“知识产权”“国家利益”。
他们甚至私下表示,中国不配接触这种级别的发动机技术。

直到2020年,一场全球疫情撕开了这层傲慢的面纱。
航空业骤停,航司停飞,罗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发动机维护收入,财报血红一片。
那一年,它宣布裁员9000人,占总员工数的17%,甚至把旗下能源部门贱卖,仅换回8英镑。
雪上加霜的是,Trent1000发动机因设计缺陷导致70多架波音787停飞,光赔偿金就吞掉22亿英镑。
更尴尬的是,疫情让零部件供应链断裂,罗罗不得不靠贷款续命。

面对破产边缘,中国再度伸出橄榄枝,投资200亿元、提供未来20年5000台发动机订单,还邀请罗罗参与中俄联合的CR929宽体客机项目。
对任何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来说,这是救命稻草。
但罗罗依旧拒绝。
CEO在发布会上硬声称:“宁可缩小规模,也绝不把核心技术交给中国。”外界听起来像是爱国宣言,实则是政治绑架。
因为背后,美国在威胁,只要罗罗与中国合作亿正策略,就可能被列入“实体清单”,禁止获得关键合金材料与软件。

当时的英国政府也附和美国的说法,媒体煽动所谓“国家安全”情绪。
就这样,罗罗放弃了唯一能让自己喘息的机会。
谈判桌上,47天的拉锯无果,双方的代表几乎是带着怒气离开。
合作流产,罗罗继续沉沦。
在这场傲慢与现实的较量中,它选择了前者。可谁也没想到,仅仅三年后,它会被现实狠狠打脸。

从全球巨头到被市场抛弃:罗罗的塌方式滑落
罗罗的问题并不是中国造成的,而是它自己困在了旧时代的荣耀里。
2021年,公司虽短暂扭亏为盈,但那只是会计手段的虚假喘息,真正的困境没有结束,通胀飙升、供应链混乱、订单锐减。
欧洲航空复苏缓慢,美国市场竞争激烈,罗罗的现金流再次吃紧。
2023年,公司再次宣布裁员2000人,出售旗下西班牙子公司ITPAero。
员工怨声载道,股价连跌。

与此同时,中国市场却一骑绝尘。
民航客运量连年增长,2023年增长率高达5.9%,预计未来十年将新增9000架飞机。
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航司市场,更是发动机维修和制造的潜在金矿。
最致命的是,中国没有停下脚步,罗罗拒绝合作后,中国迅速成立专项团队,把原本想购买的技术拆解成127个技术难点,全部立项攻关。
三年时间,国产CJ-1000A发动机在珠海航展亮相,性能直逼罗罗的遄达系列。
这意味着,就算没有罗罗,中国也能造出大飞机心脏。

罗罗当然明白这点。当他们看到中国科研团队实测数据时,震惊得无以复加。一个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市场,居然在短短几年追上来了。
更糟糕的是,美国的实体清单并没给罗罗带来任何好处,反而让它失去了亚洲的稳定供应链。
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在经济利益面前变得苍白。华盛顿口头上支持盟友,实际上却优先保障自家企业。
罗罗终于明白,它不是帝国的骄傲,而是美国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

于是2023年,一份低调的合作文件悄然签署,罗尔斯·罗伊斯与中国国航共同成立北京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公司,占地八万平米,预计2026年投产。这是它第一次在中国建厂。
这次,罗罗不再谈技术安全,不再说绝不转让。
他们公开承认,中国是未来20年唯一能带来增长的市场。光是北京维修厂,就能为他们每年带来3亿英镑净利润。
现实让他们明白技术再先进,离开市场也得饿死。

中国不再是买家,而是规则制定者
罗罗的回头,并不是孤例。
波音、空客、赛峰、GE,几乎所有航空巨头都在重新审视中国。
过去他们把中国当成装配厂、零部件供应国,如今他们意识到中国不仅有市场,更有技术与资本。
尤其是航空发动机这一领域,曾被西方视为“最后的壁垒”。
可如今,中国不仅能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,还能支撑完整的供应链,从高温合金、叶片到控制系统都能自产。这意味着,垄断正在崩塌。

罗罗当然不甘心。它想通过设厂、维修、培训等方式重新绑定中国市场,争取在新格局中占一席之地。但问题在于,主动权已经不在它手里。
现在中国不缺合作伙伴,也不缺技术输入。它更需要的是话语权——谁来制定标准、谁来掌握产业节奏。
这正是罗罗最怕的,过去它能决定中国买什么发动机,用谁的配件,未来它可能得排队等中国批准项目。
更深层的转变是思维方式的反转。以前是中国求合作,如今是他们求进入,以前是他们“挑选”合作对象,如今是中国筛选合作条件。

未来十年,中国民航市场将超越欧洲与北美,占全球新增飞机需求的四分之一。
发动机维修、零件制造、售后服务的市场总值将超过2万亿美元。谁拿下中国,谁就主导未来航空格局。
所以,罗罗不只是“回头”,而是在求生。
他们口中的“开放部分技术”,其实是一种妥协:不愿再错过第二次机会。因为错过一次,他们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。

如今的中国,早已不是“依赖进口”的角色,而是世界航空产业链的核心。
CJ-1000A只是开始,更先进的CJ2000、超音速发动机都在路上。
当西方还在计算制裁名单时,中国的工厂早已在夜以继日地生产新一代航空零部件。技术封锁在这里已经失效,因为我们自己成了源头。

结语
从“宁死不合作”到“主动上门求合作”,罗罗的转身像一记响亮的耳光,打在西方技术傲慢的脸上。它提醒世界:时代变了。
中国不再是被动的买家,而是能决定格局的制定者。
技术的门槛终究挡不住真正的创新者。
未来十年,航空发动机的竞争不只是技术,更是市场、产业链与信心的竞争。
罗罗的故事不过是一个开始,真正的巨变,才刚刚起飞。
凯丰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